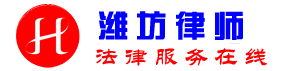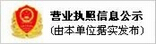我的专业背景:宪法学+政治哲学(侧重规范论证)——仝教授:政治科学?
一、法律性质: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最基层的直接民主单位
1998年组织法第3条+2009年草案第4条——“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彭真的讲话
村民会议的核心地位
区别于乡镇以上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代议民主
村民自治的个性所在
理论合理性:
(1)民主的本义(直接参与决策,选举是代议制民主的主要内容之一/王绍光《民主四讲》/卢梭(力量可以代表,意志不能代表)/托克维尔(美国的基层民主,新英格兰地区的自治精神
代议制民主是民族国家政治规模约束下的实践理性和自由主义国家理论(最小政府/最大自由,背后是资本主义导向的新教伦理)相结合的产物,但在理论逻辑上并未也不可能完全取代直接民主的理想性。
密尔的“分层民主”理论(对代议制民主和参与式民主的调和,后者与文化和民主基础的关系更加紧密),在其《政治与文化论文集》中,提出:
“一项政治活动每隔几年才举行一次,但在日常生活中公民并没有为这一政治行动做好准备。而当这一政治活动要求公民运用其智力、道德和品性时,后者却已经远离他们。”(p.229)
“我们不可能仅仅通过别人的告知就学会如何读书写字,学会骑马或游泳,但是通过实践就能学会。同理,只有通过小范围的实践大众政府的活动,才能在更大规模上学会如何运作大众政府。”(p.186)
〔J.S.Mill, Essays on Politics and Culture, Himmelfarb G. (ed.), New York(1963)〕
(2)治理结构的分权定理:辅助原则(较低单位优先决策)(这也是联邦制的理论基础)
辅助原则的宗教根源:
“褫夺个人凭自己的创意、用自己的办法所能够做到的事情,将之移转给某个群体去做是不合法的,同样,将下一级或较小群体能做的事情移转给上一级或较大群体承揽也是不公正的,同时也严重损害和搅乱了社会秩序。一切社会实体都应当辅助社会整体的成员,而不是吞并它们,也不是摧毁它们。”(1931年,教皇庇护十一世〈Pius Ⅺ,1857-1939〉在为纪念《新事物通谕》颁布40周年而宣告的《四十年通谕》)(出处:〔法〕阿兰·佩雷菲特:《信任社会——论发展之缘起》,邱海婴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56页)
二战后逐渐发展成为欧盟法上的决策分权原则和宪法上的分权原则。
辅助原则的经验主义基础:(1)决策的信息对称要求;(2)决策的责任性(自己责任的理性原则)
(3)社会化政府的理念:卢梭,全体人为全体人立法,每个人都是充足的主权分子(1945年毛泽东答复黄炎培,如何跳出兴亡的历史周期率?“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二、治理结构:建构村民自治中的“人民主权”(非代表制)
主权标志:决策机关的设置
(1)以村民会议为村民自治决策权的最高载体;
(2)以村民代表会议充任日常决策机关(以村民会议的授权为根据)
(3)以村委会为执行机关(村委会对重要的自治事项无决策权)
(4)修订草案中的监督机构主要以村委会为监督对象,属于一种执行监督
三、法律推进的主要方向:修订草案
(1)村委会的设置原则:便利群众自治(1998年法律第8条),2009年草案增加“便利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存在原则冲突,应以“便利群众自治”为第一原则(检讨破坏村民自治制度空间的“并村联组”)
(2)规范化罢免程序:最重要的突破,罢免主持机构由“村委会”改为“村选举委员会”;罢免程序的自主性(避免引入国家权力,实行真正的自治)
(3)选举委员会的独立性与功能扩张:选举委员会委员不得兼任村委会委员(修订草案),选举委员会同时负责主持罢免程序(功能扩张,还不够——应包括主持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仍由村委会“召集和主持解决不了”开会难“的问题)
(4)村民代表会议的定位问题:架空村民会议,彻底改变村民自治的直接民主方向?授权原则的控制并不充分,重要的是真正按照”便利群众自治“原则设立或调整村委会区域规模,研究如何合理化村民会议程序
(5)组织法还是“村民自治基本法”?
村委会组织法无法准确有效地涵盖村民自治的本质内涵,因为村委会不是村民自治的核心权力机构,“组织”也不是村民自治的核心程序
更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自治基本法》
反思“四大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顺序——以国家民主为原型和范本,有缺陷。村民自治的核心是“自治”,规范意义上直接对应的是“民主决策”,因而村民自治的法律应以“民主决策”为核心展开,“民主选举”只是从属性的制度。
村民自治的最高权力机关“村民会议”由每个成年村民直接组成,无需“选举”,也无需“组织”,更无需“代表”。
(6)村民自治领域是否需要“党的直接领导”和“行政主导”强化“党的领导”,强化“村委会主导”或“村民代表会议”,表面理由是“村民会议”召集难,实质理由仍然是不相信“村民”的个体理性,背后是国家控制逻辑。
是否有更好的控制?应增强司法作用的空间
修订草案第34条第1款的进步与不足:进步——撤销之诉,不足——将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排除在诉讼标的之外(修订草案第25条第2款也应有诉讼机制来支持)
修订草案第34条第3款,仅有上级政府纠正乡镇政府的干预,显然不够(应归于行政诉讼——行政权侵犯村民自治权,在操作上由县法院行政庭受理并判决,也不存在司法不独立的问题)
四、参与式民主与村民自治的关系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
基本观点:
(1)参与式民主的兴起标志着共和主义国家观的复兴(与自由主义相对,强调整体利益、公民美德、公民责任、协商理性)
(2)参与式民主的强形式(包含个体决策权)和弱形式(咨询性参与)
(3)参与式民主的共和主义导向符合村民自治的直接民主的制度个性
(4)参与式民主的程序理性可以为村民自治程序的合理化提供制度基础
(5)村民自治领域是强形式的参与式民主为主,弱形式的参与式民主为辅,根据事务重要性和影响范围,通过村民自治章程进行决策分权和责任分殊
(6)村民自治的制度重点在于决策程序的合理化
理念上: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
技术上:《罗伯特议会规则》的简化 (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孙涤、袁天鹏译)
重新审视村务公开的价值:从监督到参与 (对比政府层面:从政务公开到政府信息公开,功能拓展)
重新审视村庄组织的多元化:从个人参与到组织化参与(这种组织不宜为家庭,尽管家庭是最基本的利益共同体,但其公共性不足,不适合作为现代政治中的社会组织)
何包钢等人在浙江温岭泽国镇的协商民主试验(专家的技术辅导),乐观提出中国”有限协商民主“的制度愿景,这是推进村民自治的正确方向。
(7)村民自治中实践参与式民主的功能分析:公民化、责任化、理性化(合格的村民也将是合格的公民)
(8)对村民自治权的侵权问题和被侵权问题,宜引导向司法控制的框架(行政诉讼)——(2008年熊伟的公民建议,最高法的司法解释无法出台,涉及乡镇行政权侵犯村民自治权的法律救济问题)
五、关于仝志辉教授若干观点的批评
1、一人一票还是户代表制?
对”一人一票“的主要批评意见
(1)“和村庄社会以家户为最基本利益单位的社会结构状况产生偏离,从而导致部分激烈竞争的选举对家户基础上的农村内在权力结构产生冲击,破坏了村庄治理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从而损耗了“三自”实现的社会资本。”
(2)贿选:真的那样严重?那样重要?社会后果如何?
(3)异化为“委托投票”
因而主张户代表制。
我的反对意见:
(1)现代民主革命的基本逻辑是解放“个人”:使个人走出乡土、家庭和阶级,成为“新人”——宪法上的公民,但这个过程由于种种原因并未最终完成,户代表制以“传统”的名义和功能性的比照,意图中止村民的“公民化”进程,不合时宜;
(2)现存法律中关于户代表的规定是附属性规定,是对现实的合理妥协,而不是制度推进的规范方向;
(3)户代表制的本质是“家长制”,成年妇女乃至成年男子将丧失参与村庄政治的机会,将助长家长制乃至于家族政治的重演,不利于培育村民自治的现代公共领域,也不可能提供具有现代性质的村级公共生活;
(4)贿选问题:可治理,行政处理,司法介入,选举中的秘密投票制度;选民并未受损(如果加强罢免程序,则贿选动力会削弱,贿选当选后侵害集体利益的机会成本也将加大)
(5)委托投票:政治社会学的实证结论,可治理,不能作为改变制度原则的充足理由(存在不一定合理,更不一定符合制度理性)
(6)关于村庄的社会资本问题:基本上被文革消耗殆尽,只能通过一种现代性的民主方式获得重新生产。
仝教授在村务决策上也坚持户代表制,批评理由同上。
2、村民自治的决策权架构:村民会议还是村民代表会议?
“基于农户是村庄主要构成单位,应该重视由户代表选举产生的村民代表作用,加强村民代表会议作用;取消村民会议由本村18岁以上村民过半数参加的规定。”(仝志辉评论之二)
以村民代表会议取代村民会议显然不合法,也不合理:
(1)与村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原则直接冲突;
(2)修订草案的“授权原则”容易导致村民会议被架空(保留的两个决策事项,一个是关于改变和撤销决议的,另一个是兜底条款,没有实质意义)
(3)实践中更多采用村民代表会议并不能说明这一形式合法,更不能说明其正当
(4)采用村民代表会议决策的理由:“人数众多,居住分散”?在通常情况下,“人数”为何众多?居住为何分散?有无人为原因(行政规划,如并村联组)?村委会的设置或调整是否按照“便利群众自治”的原则执行?若此,为何“人数”还是众多?“居住”还是分散?——结论:所谓的理由不是理由,只有深刻理解村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原则是其根本的制度个性所在,才能衡量何种制度设计合法正当,也才能据此进行其他方面的调整(如规划调整)来满足村民自治的基本要求,否则就是“削足适履”,适得其反。
3、村民自治的推进依赖于示范和行政指导?
示范:村民自治需要那么多五花八门、形态各异、约束条件不同的“模式”吗?(基本版本:“中组部版”——强化村支部功能;“民政部版”——强化村委会功能),村民自治的法律主体——村民何在?
何谓“自治”?不是“照葫芦画瓢”,不是按照各种示范经验统一推广,而是在基本的法律框架内自己决定具体的决策权分配和行使程序(通过村民自治章程具体展开)。只有改变替“村民”探路和做主的“制度规划”(背后是国家中心主义)思维,村民自治才能获得可欲的发展空间。至于对村民自治的控制,主要侧重防范村民自治中多数人对少数人权利的剥夺,这方面司法机制更加优越,对村民自治体系的冲击最小。
行政指导:行政如何不干预是难题、正题。
4、“后选举治理”:正确的概念,但文章如何做?
六、开放讨论: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村民自治制度强化的紧迫性
1、从城乡二元到城乡一体:村民的公民化
可能后果——进入统一的国内权力体系和市场体系,政策性保护逐渐松弱,交易风险伴随交易自由而攀升
城市化必然意味着农村在区域和人员的意义上不断缩小,不断地以固有的土地权利置换城市的市民权(郑永年)
2、城市权力与资本以“新农村建设”为名下乡“圈地”,农民的谈判能力和权益自我保护能力将经受最要重的挑战
2010年春节的回乡体验:苏北农村 省级新农村建设规划 “以租代征” 政府+大型外来企业+村集体+村民 500元/亩/年 集体农庄
3、不稳定的农民工群体:城市化还是回乡/“留守族”的政治(未成年人+老人,是福利群体而非政治群体,这也是主张代表制的一个重要理由,但正常的城市化吸纳农民工的能力有限,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以及中央加强农村发展的背景下,农民工回乡趋势上升,有利于提供村庄政治的人力资源基础。
4、让农民首先在政治上“成熟”:后选举的真正使命/通过政治现代化带动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提高农民的政治谈判能力和运用法律的能力,抗击快速城市化的利益风险与社会风险。
(这是应中国人民大学仝志辉教授的邀请在其研究生课程中的一次讲演提纲,2010年4月20日上午10点,明德法学楼502)
【作者简介】
田飞龙,系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专业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研究员。
北大法律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