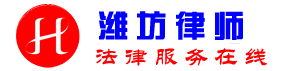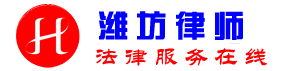禅城法院在刑事审判中发挥法官的主导作用,积极稳妥地调处刑事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附带民事争议,是司法能动性的体现,也是司法为民的生动实践。
大量司法实践表明,有具体被害人的刑事犯罪案件处理不当,往往会诱发涉法上访等不安定因素。通过刑事和解,恢复加害人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受害人受到的损害,修补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为被告人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创造条件。刑事和解制度对于妥善处理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相当的潜力。
在西方诉讼法学理论上,有所谓刑事和解制度(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一般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会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其目的是修复因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而破坏的加害人和被害者原本的和睦关系,并使罪犯因此而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在西方,这也属于新型的司法制度。
我们知道,刑法的价值在于秩序和安全,刑法价值的实现有赖于良好的立法、诉讼机制以及司法水平和社会环境,在现实条件下,刑法价值只能相对地实现,而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刑法价值的实现。我国悠久的调解历史、“厌讼”的文化传统、新时期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设定和司法实践中存在和解的事实,均有利于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建立。
但是目前我国实行刑事和解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刑事和解虽然是民事契约自由精神在刑事法领域的发挥,在和解过程中要遵循契约自由的原则,但并不意味着民事的合同规则在解决刑事和解问题上是充足的,因为当事人之间进行和解的毕竟不是简单的一般侵权行为。目前,关于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如何产生(究竟是由相关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担任还是由社会自愿人员担任,需要什么样的资质)、刑事和解可以针对哪些类型的案件(是固定在自诉案件范围内,还是在公诉案件中也予以运用)、刑事和解究竟可以在多大范围的诉讼程序上产生(诉讼前的和解是否要在法律上承认)、刑事和解调停的步骤和方式(怎样的步骤保证刑事和解制度中当事人确实自愿和解)、没有启动诉讼程序的刑事和解是否需要由司法机关加以监督(例如不经公安司法机关的私下和解)、诉讼过程中产生刑事和解是否需要司法机关加以监督(如何监督以及进行多大程度的监督)、刑事和解达成之后执行过程出现问题如何解决等等程序上的事项,在刑事诉讼法中都没有规定。
也正因为如此,东莞法院首创的刑事和解制度曾被广泛质疑和诘难,认为是“以钱买刑”。
其实,这些都可以在实践中探讨,千万别动辄扣上大帽子,一棍子打死。因为法律人都知道,这本来是个诉讼程序中的操作问题。
但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可能异化为“以钱买刑”(如有法院操作中先交罚金后判缓刑的情形)。 最高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主编的《人民法院案例选》期刊曾选登了山东某法院一刑庭法官的案例,本来该法官是从法律适用上进行自我表扬。结果责任编辑一针见血,该案中有“以钱买刑”之嫌疑。
禅城法院为了避免“以钱买刑”所滋生的“人情案”、“关系案”,甚至是“金钱案”,给刑事和解制度套上了三道“金箍咒”,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在全国法院就我所见具有首创意义。
当然,我个人认为制度约束虽然重要,当前最重要的是要从制度上鼓励法官进行刑事和解。禅城法院的努力已经使28对“冤家”“化干戈为玉帛”,但我们应当清晰,这对该院每年数千件刑事案件来说,比重仍然偏大低。我们更应看到,一是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矛盾越来越突出,社会期望值和法院自身要求也越来越高,法官办案压力大又怕出错,使调解和创新工作受限。阿花案中蔡金水法官16次电话联络的精力消耗可想而知;二是相当一些科班出身的法官学历高,但社会经验少,对当事人出现了“失语现象”:对新阶层说不上话,对青年人说不进话,对弱势者说不下话;三是法官受当前高调解率、力求减少信访、上诉申诉等司法潮流的影响,加大了心理压力。因此,必须用制度给法官“松绑”。这比规范法官行为更重要。
|